《逆清1845》[逆清1845] - 第18章 海國圖誌
說起來也是湊巧,在場的幾人中,除了康以泰是南海人,其他則都是番禺人,不過換個思路來思考也很正常,因為越秀山本身就位於番禺,學海堂自然也就匯聚了番禺士林的眾多名士。
幾人在院子裏圍爐品茗,高談闊論,除了一些學術上的問題,更多還是關於當今天下局勢的變化。
譚瑩沉吟道:「如今我看廣東城內夷人眾多,且行事多有囂張,怕是取禍之道。」
陳澧也點了點頭,道:「夷人自持武力,可橫行華夏,自然別無顧忌。」
在場眾人沒有一個是傻瓜,他們對於局勢的判斷也都出奇的一致——那就是鴉片之戰所造成的流毒已經越演越烈,廣州百姓對於洋人的態度也越發仇視,而隨着這些洋人進一步在廣東活動,恐怕將來還會鬧出亂子來。
當然,對於譚瑩、陳澧、楊黼香等人來說,他們了解到的內情並不算多,看待這件事也只能到這一層。
一旁的康以泰知道趙源對這些夷務非常精通,便主動道:「秀山,不如你也說說。」
趙源輕輕點了點頭,道:「幾位先生所言有理,我今日不妨做一次大膽猜測,將來夷人恐怕在十年左右還會捲土重來,再侵華夏。而這一次侵入,絕對沒有上次那麽簡單。」
趙源所說的,正是發生在歷史上的第二次鴉片戰爭,發生的時間正是在1856年。
當然,對於趙源的話,其他人則都是模稜兩可,靜靜等待着趙源的分析。
實際上,趙源也有相應的理由,他沉聲道:「先前夷人入侵我華夏,表面原因是鴉片貿易,而實質上則是因為我華夏長期對其形成貿易順差,西人需要我們的茶葉、瓷器還有生絲,他們只能拿銀子來買,可是他們能對我們形成大規模輸出的商品卻只有鴉片,長期以來這種貿易結構出現了失衡,導致西方的白銀源源不斷流入華夏。對於西方人而言,他們急需打開華夏的市場。」
他繼續道:「在上次英夷取得了勝利後,他們就開始了加快在華夏傾銷商品,像最主要的洋布,光是依靠價格戰就衝垮了松、太一帶的布市,導致當地很多人已經無紗可紡,即便織出來的布也很難賣得出去。」
對於生意上的事情,眾人所知不多,唯有康以泰擔憂道:「倘若如此,那些以紡紗為生的小民,又該如何過活呢?」
趙源輕輕嘆了一口氣,道:「洋布質優價廉,大肆入侵的結果,就是無數紡紗小民失去生計……他們對洋人抱有敵意也是理所當然,衝突也在所難免。」
趙源繼續道:「還有一點,上一次英夷自持武力打開了我華夏國門,攫取了大量利益,可是在這些貪得無厭的洋人們看來是不夠的,他們知道大清的虛弱,也勢必會在貪慾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再次開戰.」
楊黼香感嘆了一聲,「國事艱危至此,確實令人難以預料。」
陳澧沉吟道:「朝廷當有所變革才是。」
譚瑩卻搖了搖頭,道:「當今朝局昏昏沉沉,守成之世,治尚綜核,而振敝舉衰,非拘守繩墨者所克任也。」
這番話說得一般人就聽不太明白,但是在場眾人都是聰明之輩,自然明白這番話指的是誰。
意思主要說的有兩個人,一個是當年的軍機處領班大臣曹振鏞,另一個就是現任軍機處領班大臣穆彰阿。
對於前者,世人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評價。
「仕途鑽刺要精工,京信常通,炭敬常豐。莫談時事逞英雄,一味圓融,一味謙恭。大臣經濟在從容,莫顯奇
-
連載中116 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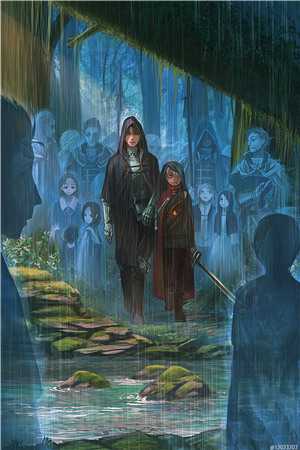
末世:囤女神,系統百倍返現大結局
「放心吧,嫂子我沒事。「我現在就帶你回家!」陳玄左手拉着柳如煙往外走,右手提着開山斧,威懾力十足。李琴原本一肚子火氣,可是看着眼前這一幕,她根本不敢說話。生怕自己多少一句,就會成為陳玄的斧下亡魂!在眾人的矚目下,陳玄帶着柳如玉直接走到了門口。嘩啦啦!可是下一秒,一...
-
連載中116 章

女帝逼我強推皇后
陳凡穿越異世,開局竟然看到皇后沐浴,本以為必死,卻沒想到皇帝竟然逼自己去睡皇后!
-
連載中116 章

秦嬈靳司堯全文免費閱讀
秦嬈做過最大膽的決定,是睡服花花公子靳司堯! 她野心勃勃想要做他的獨一無二,妄圖讓他情難自持,步步沉淪。 她使出渾身解數,斗敗鶯鶯燕燕,回首來時路,步步血淚。 她以為她贏了,可直到最後才發覺,她不過是他深海里的一條尾魚。 秦嬈火了:「靳司堯,你玩我?」 男人欺身而上:「看清楚誰玩誰?」
-
連載中116 章

初瑤葉辰澤全本免費閱讀
他是讓女人趨之若鶩的葉家大少,自恃掌控一切,直到那一晚,他寵着護着十二年的丫頭,打破了一切。 看着酣睡的丫頭,他妥協了,可是她竟逃了,消失的無影無蹤。 五年後再見,她挽着未婚夫出現在他面前,那一刻葉澤辰所有的冷靜自製,全都消失了。 深夜,他將她錮在懷裡,「初瑤,當初你先招惹了我,就該想到,我絕不會再放過你。」
-
連載中116 章

陶真裴湛全文閱讀
裴家被抄,流放邊關,穿成自殺未遂的陶真只想好好活着,努力賺錢,供養婆母,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。誰知慘遭翻車,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,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,和一雙看着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…… 外人都說,裴二公子溫文爾雅,謙和有禮,是當今君子楷模。只有陶真知道,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,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。 裴湛:「阿真。要麼嫁我,要麼死。你自己選!」 陶真:救命……我不想搞男人,只想搞錢啊!
-
連載中116 章

鑒寶大宗師免費閱讀全文
快遞員葉飛揚為了彩禮拚命工作,一遭覺醒鑒寶神技,窮小子的春天就要來了!


 上一章
上一章 下一章
下一章 目錄
目錄